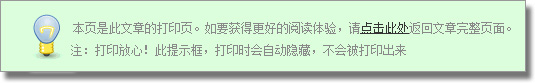留学风潮兴盛,在这个假洋博士泛滥的时代,让我们看看真洋博士是怎么奋斗的。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在美国的名校拿到博士学位,多半为两个目的所驱使——镀金的身份或是对真正良好研究环境的向往。博士,已经不再仅仅是学历的代名词,更成为了一种划分身份的象征。前者在有捷径可通达之时,多半愿意一掷千金,用金钱换取时间,凭空购买一张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反正只要烫金了的证书上署着大名,“博士”的名头就已到手;后者却选择寒窗苦读,从准备、申请、入学、考试、实验、论文、考核到最终毕业,一个人在异国的上千个日日夜夜,换回的是一张薄薄的学位证,还有这些年的经历与知识,一个人总归骗不过的,就是自己。
做一个博士,难;做一个真正毕业于美国名校的博士,更难;做一个货真价实的女博士,难上加难。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刘瑜在文章里这样写,“我们是女博士,社会声誉已经这么低下了……整个社会都笑话女博士,说‘女博士丑’,‘女博士呆’,‘女博士是第三性别’……”但无论是刘瑜,还是芝加哥大学细胞生物学专业博士桔子,都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成为女博士这条路。
中国人成了美国理科博士的中坚力量
在美国呆了6年后,桔子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在细胞生物学界,这已经是极快的速度。虽然规定的学制是5年,但真正能如期毕业的,实属凤毛麟角。同实验室一起攻读博士学位的同学里,她是第一个毕业。另一个人稍晚于她,在研究还没结束的情况下,转成了博士后。
这是在美国极为普遍的一种做法,美国的博士后职位并非更高一级的学位,而是对博士学位的一种补充,是为取得博士学位者在科研机构继续从事研究而设置的一种过渡性职位,刘瑜也在哈佛大学做过一年博士后。
而桔子的其他同学则还在实验室里继续为了毕业苦苦奋斗。“最高纪录是有个人10年才毕业,而且毕业时我还帮他画了两张图。”在国内轻轻松松“混到毕业”的故事,在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国外名校,近乎天方夜谭。
桔子毕业于北大,在生物系,有着出国的传统,80%的学长都选择了继续出国攻读更高学位。大二时,大家都去考GRE和TOFEL,她也跟着好朋友一起上了考场。天性喜欢科学的她整天泡在实验室,觉得“去那儿很快乐”。在不带太强目的性的情况下,就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几篇论文,这为她最后成功申请到芝加哥大学硕博连读奠定了基础。
在她念大学的年份里,大学的竞争还不似如今一般惨烈,目的性也非如此明确。毕业后,桔子还时常能收到学弟学妹们发来的Email,一年更比一年来得迫切与热烈,言辞恳切地希望她传授成功经历,有些人极强的功利心让她心生感慨,“好像就是为了出国怎么怎么着”。
现实情况是,中国学生的确构成了类似生物、物理、化学等传统理学学科的美国博士中坚力量。芝加哥大学作为美国北部名校,并没有招收中国人的传统,与南部许多学校比起来,“芝大算中国人少的”。但在桔子就读的生物系里,50多个人中包括了6个中国学生。至于化学、物理和统计,“上起课来和在中国上课似的。”
究其原因,美国人多半不喜欢申请这些科研学科,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却很难立刻收获成效。一张博士证书背后,有读不完的文献、写不完的论文和做不完的实验。
而且,这些学科招收学生“都是需要人手干活儿的”。勤恳的中国人和印度人,才是首选。在美国,类似生物这样的学科,硕士与博士本是一体,5年才是一个完整的学制,中间并不会授予硕士学位。“你要真想拿那么张证,体验一把毕业的感觉,也可以在学习2年后向学校申请,先发硕士学位给你,再继续念博士。”但大多数人都明白,一个破折号并不等于句号。
极其严苛的高等教育
5年的学制看起来漫长,其实几乎所有的课程都被安排在了第一年。芝大地处美国北部,天气寒冷,一学年被分成了4个学期。桔子要在这4个学期中念完规定的9门课,常常感觉还没怎么开始学,就已经要期末考试了。而且,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就要在学习的同时开始找寻自己的实验室,在数家实验室都实习过之后,她才能确定自己未来数年间真正的归宿在哪里。
从第二年开始,学校就不会再安排课程。桔子也找到了自己的实验室,但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现自己在数学、物理等学科方面仍然有所缺漏,会影响到实验进程,此时的学习就全靠自己主动了。
实验每向前推进一步,背后支撑的就是大量的原文文献和扎实的理论基础,而这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难以计数。桔子的日常生活,基本由实验室与宿舍两点一线构成。早上七八点到实验室,“晚饭肯定要在那儿吃了”,头两年,到第二天凌晨也是有的。在美国,高等教育极其严苛,桔子形容,自己的导师们“很纯粹”,是“真正的科学家”,将每一个学生都当成科研同事来要求。而在科学的世界里,没有情面可言。即使被同学形容为“不在中国,就在实验室呆着”的桔子,也有过被主任骂哭两次的经历。
在芝大生物学系,对博士生的学习有着相当严格的考核。第一年的9门课程中,3门不及格就必须退学。而在第一年和第二年中,学生都必须分别作出两个大项目的设想,类似于国内论文的开题报告,这两次考核一旦通不过,等待你的只有退学。即使是在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实验的后面数年间,实验室主任每半年都会和老师一起组成评审委员会,与每一位学生单独座谈,考核学生在过去半年里的实验成果、未来半年的实验目的与计划方案。一旦发现有学生脱离进度太远,在劝诫和督促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也只能劝说学生离开学校。
有些人会在中途选择放弃。早在第一年中,就有学生发现自己无法胜任学术研究的压力与强度,及早选择转系或是退学。而学完了第一年所有课程的学生,老师“觉得他挺好的,就是没办法再念下去了”,解决方案是颁发给他硕士证书,但建议他自己选择离开。还有些人的学习态度令导师们忍无可忍,迎接他们的就只有被开除。
“3种情况我都碰到过,”桔子说,“所以我们系起码有3个人没毕业。”
幸好,美国有着良好的科研环境。桔子形容自己的实验室老师们都很有“风度”,大家是互相扶持和支持的关系,而非恶意竞争。每个人的实验内容都不尽相同,所以能从不同角度向对方提出诚恳的建议。她毕业回国后,同组的印度同学无私地替她承担了部分没有完成的任务。
毕业前一天,做完实验,桔子离开实验室,惊奇地发现实验室主任等在外面,一脸诚恳地望着她,告诉她,“以后但凡有需要帮忙的,一定要告诉我。”
“这真的挺意外的,因为他的推荐和帮助特别有信誉。”在结束了6年的苦读生涯之后,桔子正式成为博士。她选择了回国,她的下一站,是科学松鼠会。
“在这儿(科学松鼠会)做个女博士没什么奇怪,这儿的这种人多了。”她哈哈笑起来。